
国外电影名的中译,是个艺术再创作。整整30年前,第一部好莱坞分账大片引进国内,轰动一时,比起再直白不过的原名《The Fugitive》,译名《亡命天涯》也贡献了吸引力。还有《魂断蓝桥》与《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人鬼情未了》与《幽灵》(GHOST),这类比较不胜枚举。有趣的是,除非是传记片,否则在中文语境中主人公的名字很少能当得起片名,《Thelma&Louise》(中文就译为《末路狂花》)、《Leon》(《这个杀手不太冷》),若是直译过来做片名的话,就定会被一些中国观众追问喋喋,那片名里的她们/他是谁啊,言外之意是——她们/他也能作为片名?中国的电影片名本身是有点题的使命的——说起来这可以作为一个文化比较的研讨线索。
所以能对照着看原文还是会多不少乐趣。比如一语双关,历来是翻译中的难题,妙处常就丢失在跨文化中,遗憾地没能跨过来。比如《Hidden Figures》的Figure可以理解为兼有人物和数字二义,而Hidden既在说隐蔽也暗指被无视。倘若片名中的人名还包含一层双关,就会更增难度。比如,你看这个——《Free Guy》。
Guy(盖伊)就是电影中的主人公的名字。但也可以当成是个通称指代,他就是个“伙计”,是想不起名字来时说的“那谁”或“哎你”。这名字蛮符合影片给他的角色设定,毕竟他就是一个银行柜员NPC(非玩家角色,Non Player Character),同理他的保安朋友名叫Buddy(巴迪),真是哥们儿。影片的主线是讲述Guy(盖伊)怎么就得获自由(Free)的“NPC觉醒记”,但中文片名没有傻傻地译作《盖伊得自由》,而是《失控玩家》,醒目点题,还蹭一下《头号玩家》的热度。
但较个真儿的话,这个中文片名得再斟酌。内容跟游戏有关的电影,片名都想带上“玩家”二字引流,但这部影片中失控的却真不是玩家(Player),而恰是非玩家角色(NPC);更何况,Free来自于影片中的游戏场景Free City(自由城),本身是自由与解放的意思,立场是向着盖伊和巴迪这些个NPC一边的;你用“失控”来意译Free,可就妥妥地是站在NPC的对(立)面了。

杨斌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经管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 著有《企业猝死》《战略节奏》(合著)《在明明德》(合著),译有《变革正道》《要领》《教导》等。插画:邵忠
不管是自由还是失控,撇开立场不论,情节事实倒是一致:作为服务于剧情需要增加游戏丰富性而存在的NPC,本来是一段道具人“程序”,一段因AI而能变得更好玩的程序,但因为ai(爱),突然就脱轨了,觉醒了。然后是大闹天宫(自由城),NPC大团结,替“人”行道,最终人“机”情未了。
就算不在AI时代,也有类似的觉醒发生。“喜人奇妙夜”里“四士同堂”的作品《八十一难》,觉醒的闪电就照在了气质最像是个伙计(Guy)的沙僧身上。“沙”这个姓,意为众多,平常普通;沙僧真的是西游取经团队中存在感最弱且最没有背景的成员,任劳任怨挑担牵马,几句台词循环播放,“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师父(师兄)说得对”。作为西游路上的NPC,沙僧无所欲,维护成本低。扪心对照一下我们头脑里服务于人类主人的忠耿机器人的模样,定不会是猴哥或八戒,而就会是沙僧(们)。
“小透明”沙僧在18分钟的《八十一难》里,经受着师父和两位师兄的“设计”与“激励”,最终没有被“取经”这么一个外在目的而驱使,为凑八十一难而破坏“不作恶”的绝对律令,率先立地成了佛。新颖的视角,让NPC沙僧走到了舞台中央成了主角,为西游衍生剧又算是开了个从0到1的先河。只不过,机器人(沙僧)究竟是因为遵循了忠诚于“大义”的第一性原理而成了佛,还是因为超越了听从师父师兄指令的NPC安排而得道永生?不同观众自有不同的领悟。成佛后的沙僧,终还是要回来帮助转世后的师父完成取经大业,就如同失控(自由)了的盖伊最终选择熄灭自己以恢复秩序,让觉醒派革命阵营好一片叹息。
Guy和沙僧,不只是在虚拟世界和取经神话中兢兢业业,负重背锅;这样的功能角色,在人类的世界中更是众多组织中稳定的绝大多数。《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你可能会觉得这部电影很陌生,但如果说到“第25号底片”,不知道你想起来没有?Walter Mitty(沃尔特·米蒂),这位普通上班族的名字在中文语境里仍然是没有资格上片名的,而译名《白日梦想家》更像是刻画没有蜕变之前的米蒂(Mitty),跟摄影师最觉宝贵的25号底片的精神气质正相悖。这也无怪乎影片公映后,“寻找你的25号底片”转眼间就通了电,连带着“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般的感触,成为“脱轨”行动时的接头暗号。
隋三藏对沙僧的“终一世度一人”多少有些强行上价值,但这个“度”字,用在西恩潘剪下第25号底片来“度”如Mitty般的芸芸“宅”生上,却也不违和。Guy、沙僧、Mitty,他们跳出了身处其中的NPC函数,找到了“人本之用”(human use),获得了重启新生。通过增加多样性和可能性而非程序性和效率性这些“理解人的壮丽飞跃的关键所在”,他们的脱轨、觉醒,将人类社会与蚂蚁社会区分开来。用诺伯特·维纳70年前在《人有人本之用》(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里的原话来说——
“我是相信人类社会远比蚂蚁社会有用得多的;要是把人判定并限制在永远重复执行同一职能的话,我担心,他甚至不是一只好蚂蚁,更不用说是个好人了。那些想把我们按照恒定不变的个体职能和恒定不变的个体局限性这一方式组织起来的人,就是宣判了人类只该拿出远低于一半的动力前进,他们把人的可能性差不多全部抛弃掉了,由于限制了我们可以适应未来偶然事件的种种方式,他们也就毁掉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可以相当长期地生存下去的机会。”
有些长也许还有点儿绕,但这段话却着实是维纳把书名取作《人有人本之用》的核心。
觉醒何以发生?回看《八十一难》和“第25号底片”,让Guy、沙僧和Mitty们这些个NPC觉醒,不再局限在“恒定不变”中的同一“职能”重复执行/终此一生的,不是大写的AI(人工智能),而是小写的ai(爱)。爱自然爱偶然、爱他人爱自己,爱让他们不计算,把时间精力兀自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有ai(爱),才有AI的人本之用,才有地球上可以长期生存并进化开来的人/机,玩家/NPC,蚂蚁/佛。
维纳像是盯着当下与我们似的一字一顿地说:“我们是如此彻底地改造了我们的环境,以致我们现在必须改造自己,才能在这个新环境中生存下去”。改造自己,得要有着对机器更加好奇、理解和与共的态度。还是从翻译说起,AI赋能下强大的co-pilot,常被直译作副驾驶,而我们人则是captain(机长),主副分明、主仆显然。你是从属、服务的啊,供差遣的工具啊。但也许这时师父会双手合十一本正经地说,captain和co-pilot,“为师觉得是一样的”。
七年级的小同学必读《西游记》,我请他看看《八十一难》,老书也该有新的充满想象力的打开方式。他跟沙僧一样问我,为什么非要凑81这个数不可?于是七年级的小同学说要做个访谈,我给他讲起第25号底片的故事,他问起我为什么Mitty需要底片这个东西?我的回答是,大概只不过是因为81和25是两个美好的平方数,而即将到来的2025年恰恰好是81和25这两个平方数的乘积的缘故。
妙处还在,2025还是个难得的“分久必合数”(2025分成20和25后,加和平方后又得到2025,你可以再试试81~),而下一个“分久必合数”年份要等到整整1000年后的3025年呢,不知道那时我们还会不会再一起度过。闭上眼且向远望去,畅想一下吧,毕竟作为“这个在劫难逃的星球上的失事船只中的旅客”,我们“可以采取合乎我们身份的态度展望未来”。
“明天一早,我猜阳光会好”;
凭着ai,“我要把自己打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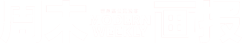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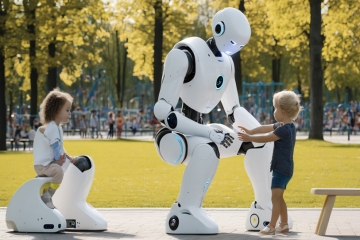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