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宽(bandwidth)的宽字,自定义了价值观,价值基于观的域,宽,才是硬道理。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也越来越习惯了很多个零,熟悉了以兆、千兆为计量单位的带宽。用得上用不上,获得感和兴奋总是有的。
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速率有多低,加州理工学院的前瞻研究在标题里用了无法忍受(unbearable)来形容——仅为10比特/秒(10 bit/s或10 bps),这是认知带宽的量级。读到的人多少还是有些泄气的,意识到碳基还远没有进化到位。
同时研究也发现,人类感知系统的带宽却不窄。拿人类的视觉系统来说,每只眼睛拥有600万个视锥细胞,每个细胞可以传输约270比特/秒的信息,总输入容量达到令人惊讶的3240兆比特/秒。即使经过视神经的初步处理,信息传输量仍保持在每秒100兆比特/秒的水平,这是感知带宽的量级。
两相比照,就意味着从感知到认知,大脑将信息筛选、压缩到亿分之一,感知到的是实际认知的一亿倍,竟然得一而漏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之所以会发生这么高比例的筛选、压缩,研究人员认为,存在着外脑以并行工作、内脑以串行工作的区分。注意,这里的外脑、内脑,是个概念性的区分说法。这是人类长期进化的结果。居然:大脑的核心功能可能并不是处理更多的信息,而是更有效地筛选、压缩信息。这句话,值得反复读读,想想。
按照这个思路,值得延伸开来,多问一个问题:阅读,是感知还是认知?这关乎我们对于“阅读的带宽,到底有多宽”的正确判断。如果侧重功用性,衍生问题还可能包括,够不够宽,如何更宽?
这就需要细究一下:在人类的阅读过程中,感知与认知层面究竟经历着怎样复杂且精妙的过程?
我们想当然地会认为是用眼睛看书——大多数时候,除了听书之外。
“阅读的过程始于书页反射的光子撞击视网膜的那一刻,而视网膜却不是一个匀质的感受器。只有名为中央凹的中心地带,才是视网膜中唯一拥有密集的、对光线高度敏感的、高分辨率的视觉细胞的区域,视网膜的其他区域只具有较低的分辨率。”
“正因为需要把文字放入中央凹来阅读,眼球在阅读的时候需要不断地移动。我们必须通过注视点的移动,用视觉中最敏感的区域来“扫描”文本,因为只有这一区域的分辨率高到足够识别文字。然而,人的目光并不是匀速不停地在书页上移动的,恰恰相反,目光总是一小步一小步地移动,我们称之为眼动——每秒钟4~5次的跳动,不断地将新的信息带入你的中央凹。”
这就是说,事实上,跟看风景不同,我们每次只能从书页上提取少得可怜的信息。
而且,阅读中,用眼看只是个起点,提取信息后进行理解,才算是个相对完整的认知过程。很多时候,不能理解,也就没法继续,就会返回头去再读再想。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听书,你需要停下来,倒回去,再听一遍某一段的缘故。
所以,阅读是用脑的,甚至是很烧脑的,更准确地说,是很用认知“内脑”的,也很大程度上受到筛选与压缩机制的制约。
阅读中经常发生的代入,联想,共鸣,通感,想象,这都是高级的思维形式。
可能你读到的是一段人物对话,或者景色描述,慢阅读中的“脑补”,却让它立体,让它丰富,让它活泼泼地,让它是你的。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完全可以说,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共创”的过程。共创的带宽,勾勒出、幻生出整个世界、全观情境的速度,值得专门去测量计算一番。
共创也是个没有什么能夺走的、不可复制的个人化的体验。
两千四百年前,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不满于写作与绘画的“离身”性,“好像是活着的,但如果有人向它提问,它却只会沉默。”“如果你对所说的内容提出质疑,你想了解更多,它们却只能重复原来的那一套话。”“而且,一旦书被写下来,每一段话都会到处流传,传到那些理解它的人那里,也传到那些与它无关的人那里。它不知道该对谁说话、不该对谁说话。”
柏拉图期待的是被“该读到的人”正确地理解,并能持续展开延伸性的对话。
对柏拉图纠结于“谁该读到”这一点的立场,我尊重并保留看法,但柏拉图所期待的所谓的“书被正确打开的方式”,现在正在每一个阅读者身上发生,或以默会向内的方式,或以生动于外的方式。
 杨斌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 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 著有《企业猝死》、合著有《战略节奏》《在明明德》,译有《变革正道》《要领》《教导》《沉静领导》等。
杨斌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 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 著有《企业猝死》、合著有《战略节奏》《在明明德》,译有《变革正道》《要领》《教导》《沉静领导》等。
我曾无数次听到周围有人说,未来脑机接口技术成熟了,脑子插上个芯片,大中小学教材、名著经典大百科,就“嗖”一下子装进去了,不用读,多省事儿。
对这些,我也要尊重并保留看法,并回应说:持这个说法的人,是该有多不懂阅读,不爱阅读。他们就像是说自己热爱运动,却只想知道比赛结果或者只爱看比赛集锦的人一样;也像是说自己热爱电影,却满足于三分钟听人讲故事情节梗概的三倍速还快进的人一样。
阅读在过程中带给阅读者的快乐体验,阅读者在过程中的共创对世界的丰富,阅读者以书写以讲述或以人生行动来与作者进行的对话,这都是阅读的有机组成。它们“嗖”不了,这不是带宽的问题,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碳基本色。
说到了“嗖”,这里还想顺带区分在生活中常有不同理解指向的词:碎片化阅读。有的人说的碎片化阅读,指的是在繁忙中挤时间阅读,把碎片化时间充分整合,用来阅读,当然必须要有场景迅速切换的技能来支撑,毕竟阅读是需要沉浸其中的;还有人说的碎片化阅读,更准确地表达,应该说是看碎片信息。我这里执意用看而不是读,指的就是浏览性地看各种碎片,浮光掠影,只言片语。前者是想把零敲碎打的时间拼接,让阅读更长线,更沉静;后者是把认知和情绪零敲碎打化,客观上专注力更短,人也更浮躁。
回到开始说到的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长期持续阅读本身,究竟会给从外脑到内脑的高比例筛选、压缩机制带来什么影响呢?之于从海量的感知输入中提取出对行为真正重要的精华信息,会不会自发形成什么偏好,实现某种塑造呢?
一个坚持慢阅读的人,跟一个每天对着许多电视频道不停切换的人,跟一个只看碎片并回之以碎片信息的人,感知带宽和认知带宽会逐渐地发生着结构性分化。对某个人和某一代人来说,谈不上进化,但可以称之为训练,特别是在越来越长的生命周期中,会带来大脑的重构(rewiring)。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成年人的阅读习惯,以及他的阅读书单,都是隐私。如果他不愿意分享,那是属于他自己的自由王国。有时候,当有人愿意分享出来,也许是他正期待着某种对话。在阅读中的那些与作者的共创过程,也许会借由这些对话得见,经由更多的对话延展。那些书,那些阅读体验,以及那些对话,扩延着人类整体的带宽。
相对应,值得思考的是,公众领导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推荐,是否具有某种公共属性?领导者的书单(有时候还有歌单),是否也是一个与民众进行沟通,并发挥社会领导力的途径?
很多领导者可能没有意识到,随着自己的角色转变,也需要对阅读带宽重新审视。在《要领》一书中,汉尼斯提到自己在“阅读带宽”上的一次扩延。曾为2017年图灵奖获得者的他,在接任斯坦福大学校长后曾说,“你不仅要学习与你的角色以及你的行业直接相关的主题,更要涉猎那些能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加全面、更有智慧的人的通识。”我不好评价这个阅读带宽的扩延,对于汉尼斯这样一位由专业人士成长为面向世界擘画未来的组织的领导者来说,所起到的重构(rewiring)作用,但作为持续成长的领导者,有这样的阅读自觉、带宽自省,是非常关键的。
毕竟,you are what you read,阅读既塑造人,也塑造历史,这在茨威格的视角看是一定的——关键人物的阅读,影响着人类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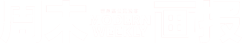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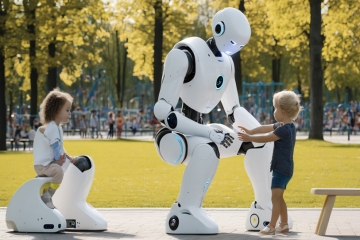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