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ekly
2023年国际布克奖首次颁给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Georgi Gospodinov),他的获奖小说《时间庇护所》(Time Shelter)讲述了一个国家,整体沉浸于过往时光的故事。戈斯波丁诺夫承认,自己的写作动力主要受到了2016年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影响,“我写这本书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感到我们的时间发条装置出了错”。作为冷战后译介最多、最具国际声誉的保加利亚作家,戈斯波丁诺夫广泛创作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擅长复调叙事,擅长将东欧刚刚过去的记忆与欧洲和世界的当前焦虑串联起来。
 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
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
人是怀旧的动物。人们建造集体的纪念碑,无声缅怀那些可能已经鲜有人问津的过去;也书写个人的回忆录,在生命远未完结之时便一遍又一遍嗟叹岁月流离。普鲁斯特用一部《追忆似水年华》写尽对于往事和故人的无限思绪,茨威格则以《昨日的世界》抒发着一个欧洲人的文化回忆。还有无数科幻作品、童话作品想象一种“时光机器”,只要坐上去、按下按钮,人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回到自己想要的过去。这种想象至今仍充满诱惑力。最新的版本是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的小说《时间庇护所》:一间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提供治疗的时间诊所,允许患者停留于令他们感到安全的年代,直到它的疗效之显著令所有健康人也要慕名前来,以期逃避当下生活的诸多苦楚。
《时间庇护所》在今年5月刚刚获得国际布克奖。这是戈斯波丁诺夫第四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布克奖的保加利亚语作品。评委会主席莱拉·斯利马尼(Leïla Slimani)称之为“一部充满讽刺和忧郁的杰出小说”,令人质疑“我们的记忆是如何成为我们的身份与亲密叙事的黏合剂的”,“但这也是一部关于欧洲的伟大小说,在这片亟需未来的大陆,过去被重新创造,而怀旧成为毒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像保加利亚这样处于西方与共产主义世界意识形态冲突中心的国家之视角”。《纽约时报》书评人阿德里安·内森·韦斯特(Adrian Nathan West)则敏锐地指出了小说中的政治隐喻,“在阅读这一切的时候,不可能不想到英国脱欧和MAGA(特朗普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甚至普京的大俄罗斯民族统一主义背后的保守情绪”,然而,戈斯波丁诺夫却并不诉诸某种粗鲁的政治讽刺,因为“他确信回到过去无法消除当下的冲突”。
 2022年6月,戈斯波丁诺夫与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对谈。
2022年6月,戈斯波丁诺夫与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对谈。
怀旧主义的庇护所
《时间庇护所》在概念上似乎遥远地呼应着T·S·艾略特晚期代表作《四首四重奏》其一《烧毁的诺顿》中,那段充满神性与超验的开端:“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含在过去的时间/假若所有时间都永远存在/所有的时间就再也都无法挽回。”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高斯汀(Gaustine)的治疗师,为了帮助治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在苏黎世开办了一间“过去的小诊所”——之所以选择苏黎世,是因为高斯汀相信瑞士历来的中立性使它能够“毫发无损”地穿梭于不同年代,“不会让你困在某个时代的特殊印记中”。这间“过去的诊所”每一楼层、每个房间都各不相同:特定的香烟品牌、灯罩、壁纸、档案杂志……它们以完美主义者的标准和强迫症患者对细节的掌控度装点着不同房间的布置,配合情绪与意识的调节,力图重现出“与患者的内在时间同步”的历史空间,帮助他们“回忆”起自己生命过程中被“肢解”的部分,从而使他们暂居于这片临时打造的安全区域之中。当高斯汀的病患获得疗愈的奇效时,他的传奇疗法也声名远扬。欧洲各地纷纷开设新的时间诊所,其中就包括保加利亚。
但大面积的效仿让高斯汀开始担心人们在不同年代间过于轻松穿梭来回的潜在心理影响,他的解决方案是暗示人们建造一座完全属于过去的城市乃至国家。他抱怨人类对于21世纪的梦想失败了,“未来的失败在部分程度上也是医学的失败”,他如此宣告。在高斯汀和他的许多拥趸看来,“过去”不仅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良方,也是应对当代社会失范与焦虑的良策。于是,“怀旧热”席卷欧洲。就如同现实中的英国脱欧一样,小说中,每个欧洲国家也都在用公投的方式决定应当回到哪个年代,因为这种选择无非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的过去中,这是我们已经做过的;或者让我们自己分崩离析,互相残杀,这也是我们已经做过的”。公投的结果,瑞典选择了1970年代,那个属于ABBA乐队和宜家的扩张十年;多数中欧国家选择了1980年代末期,一个空气里都洋溢着政权更迭在即的乐观希望的时期;而在保加利亚,希望回到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与沉浸在1876年战胜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冲突,结果形成了一种“穿着马裤的男人躺在头上打满了发胶的女人旁边”的奇怪混搭风潮。
 2023年2月1日,保加利亚民众在索菲亚纪念碑前纪念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政权受害者纪念日。
2023年2月1日,保加利亚民众在索菲亚纪念碑前纪念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政权受害者纪念日。
进入一个过去的时代往往意味着接受特定的心理训练,忽略过去的某些不美好部分——“你必须不断记住,你应当忘记的是哪些事情”——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另一个极端:“一个社会遗忘得越多,就越是有人生产、销售虚假的记忆,并用这虚假记忆填满空余的空间。”戈斯波丁诺夫以此奚落人们对于那些从未真正存在过的黄金年代的热望,也对应着小说叙述者G·G在苏黎世初遇高斯汀时在那间小小的“过去的诊所”注意到的:“过去不只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有时它是你刚刚想象出来的事。”小说中有不少令人哑然失笑的黑色幽默:一个前秘密警察成为了他曾迫害、举报之对象的记忆假体,帮后者存储着那些本不属于他的幸福时刻;而一个罗马尼亚病人获得慰藉的方式也并非忆起了自己过去的经历,而是他所幻想的美国生活。正如英国小说家、批评家帕特里克·麦吉尼斯(Patrick McGuinness)所称,在《时间庇护所》中,怀旧“并非关乎你所拥有之物的记忆,而是关乎你想要之物的记忆:这是一张来自一家绝不存在却不知何故总能兑付的银行的倒填支票”。而在内森·韦斯特看来,尽管戈斯波丁诺夫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对明显来自过往之物的同情”——过时的物品、老牌子咖啡、被摈弃的古董唱片——但他断然拒绝将全球化、移民与现代化当作导致前者灭绝的“替罪羊”,“我们都是毁坏历史的同谋,而倒退到过去仅仅意味着愈演愈烈的不宽容”。
某种意义上,《时间庇护所》也像是为哈佛大学斯拉夫比较文化教授斯威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的著作《怀旧的未来》所描绘的一幅精彩插图。早在这部20多年前成书的作品中,博伊姆便一针见血地指出,“20世纪始于未来派的一种乌托邦,却止于这种怀旧病”。她认为,眼下“全球都在流行这种怀旧病,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拥有一种集体记忆的共同体情感,渴望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获得一种连续性”,它“承诺重建今天诸多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一味主张的理想家园,引诱我们放弃批判思考,代之以情感团结”,而“当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逐渐复兴的民族主义,是这种怀旧病的 ‘亢奋’变态,并最具有危险特征。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通过回归及借助民族主义的符号和神话,有时甚至通过把各种阴谋理论改头换面,而编造出一种反现代的历史神话”。在《时间庇护所》的后半部分,当一系列全民公决将欧洲分割成不同的时代,时间性的联盟取代了地区性的联盟;而随着各国努力规范各自的外交事务,边界也开始关闭。旧的怨恨不断恶化,直到一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的拙劣重演将欧洲大陆推向了“第二场一战”的边缘。怀旧被彻底“武器化”了,而曾经作为救赎的时间最终成为一片废墟。

国家与时代寓言
《时间庇护所》继承着戈斯波丁诺夫一以贯之的保加利亚民族书写,也与他土生土长的保加利亚身份密不可分。1968年,戈斯波丁诺夫出生于与土耳其相邻的边境小城扬博尔。由于父母常年在镇上当兽医和老师,他的童年时光主要是与祖父母在乡下村落度过的。他记得那种时时担心自己被“遗弃”的恐惧感,也记得后来被父母接回镇上后独留于地下室公寓里的孤独感。“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层面来谈论那时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缺陷——不仅是商品和实物的稀缺,也是亲密对话和真理的稀缺。”接受《卫报》采访时,戈斯波丁诺夫这样回忆起童年经验带给他的漫长阴影。但不可否认,也是那段时期培养了他的文学萌芽。父母的地下室公寓里有一个偌大的家庭图书馆,那里包罗万象,无数学校和家庭教育中未能教给他的知识正待他的发掘。而他讲故事的能力也在那时开启:坐在地下室,看不见上半身的一双双大腿从窗外经过时,他便在脑海中想象一张张面庞,一个个人物,虚构着他们千姿百态的生活。他尤其喜欢阅读一些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故事,“为什么?后来我自己意识到了:因为我不希望主人公在故事最后死去。只要你还在讲述故事,你就还活着。我们的故事创造生命,也抵抗死亡与邪恶”。
出版过两部颇受好评的诗集后,戈斯波丁诺夫在1999年推出自己的首部长篇处女作《自然小说》。该书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被翻译成21种语言,蜚声国际。美国当代小说家加斯·格林威尔(Garth Greenwell)评价,正是《自然小说》将戈斯波丁诺夫“推到了他那一代保加利亚作家的前沿——他们是保加利亚向民主过渡后涌现的第一批作家”。《自然小说》探索后共产主义时代保加利亚一名年轻作家的生活,具有鲜明的元小说风格,各种插曲、离题、寓言、清单与沉思构成的片段,松散地围绕着叙述者婚姻的解体。“我不谦虚的愿望是塑造一部关于开端的小说。”叙述者开宗明义地说道,但似乎也一再颓丧地质疑小说本身,“当崇高不复存在,我们所拥有的仅剩日常生活时,小说的概念还如何成为可能?”

戈斯波丁诺夫在2012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悲伤的物理学》带有更加深刻的保加利亚民族属性。这部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经济学人》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幸福地理学》的文章,其中宣称保加利亚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地方”。戈斯波丁诺夫在后来的采访中坦率地回答:“最终,我的主人公就是在讲述关于这样一个地方的故事,这个最悲伤的地方,以及他如何处置自己的悲伤。他把它们按顺序列好,描述它们。”在戈斯波丁诺夫看来,“保加利亚的悲伤”是切实存在的困境。他笔下保加利亚语中的tuga,就如同奥尔罕·帕慕克笔下土耳其语中的hüzün、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笔下俄语中的toska一样,表述着某种难以用英语等其他语言准确翻译的独特的哀愁或悲伤。“一种对尚未发生之事的渴望,一种意识到生命正悄悄溜走,而无论出于个人的、地理的还是政治的原因,某些事都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顿悟。”戈斯波丁诺夫这样解释他的tuga。格林威尔认为,这种未经验证的生活确实也只有在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地平线如此频繁地被重新划定,到处都是 ‘模糊、抽象的意识形态’与它们的失败承诺”的国家,才会产生特别的共鸣。
哪怕就现实意义而言,这种悲伤并非完全为保加利亚所独有。从《悲伤的物理学》到《时间庇护所》,可以看出戈斯波丁诺夫的“保加利亚悲伤”正渐渐迈向“欧洲的悲伤”,乃至“世界的悲伤”。今年4月接受国际布克奖提名采访时,他详细介绍了《时间庇护所》的成书与2016年前后世界时局的密切联结:这是一种“感到时间发条装置出了错的感觉”,“你可以在空气中闻到焦虑的气味,用手指就能触碰到。2016年之后,我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民粹主义危机日益侵袭,美国和欧洲纷纷打出 ‘伟大的过去’这张牌,令全世界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这让我感到愤怒”。很难不让人想到波兰裔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怀旧的乌托邦》中所提到的,在今天,尽管“金融、产业、贸易、知识、交流以及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都已经全球化了”,然而“用来管理人类状况关键因素的那些政治工具,仍然是地方性和自我参照性的”,“这是人类面临的最难解决的困境”,一种“元困境”。鲍曼在写完《怀旧的乌托邦》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了。然而七年后,在一个人工智能和元宇宙已经汹涌而来的时代,这个根植于现实的致命“元困境”仍然未能解决。
BOX
《故事走私贩》
作者:Georgi Gospodinov
出版社:Sylph Edi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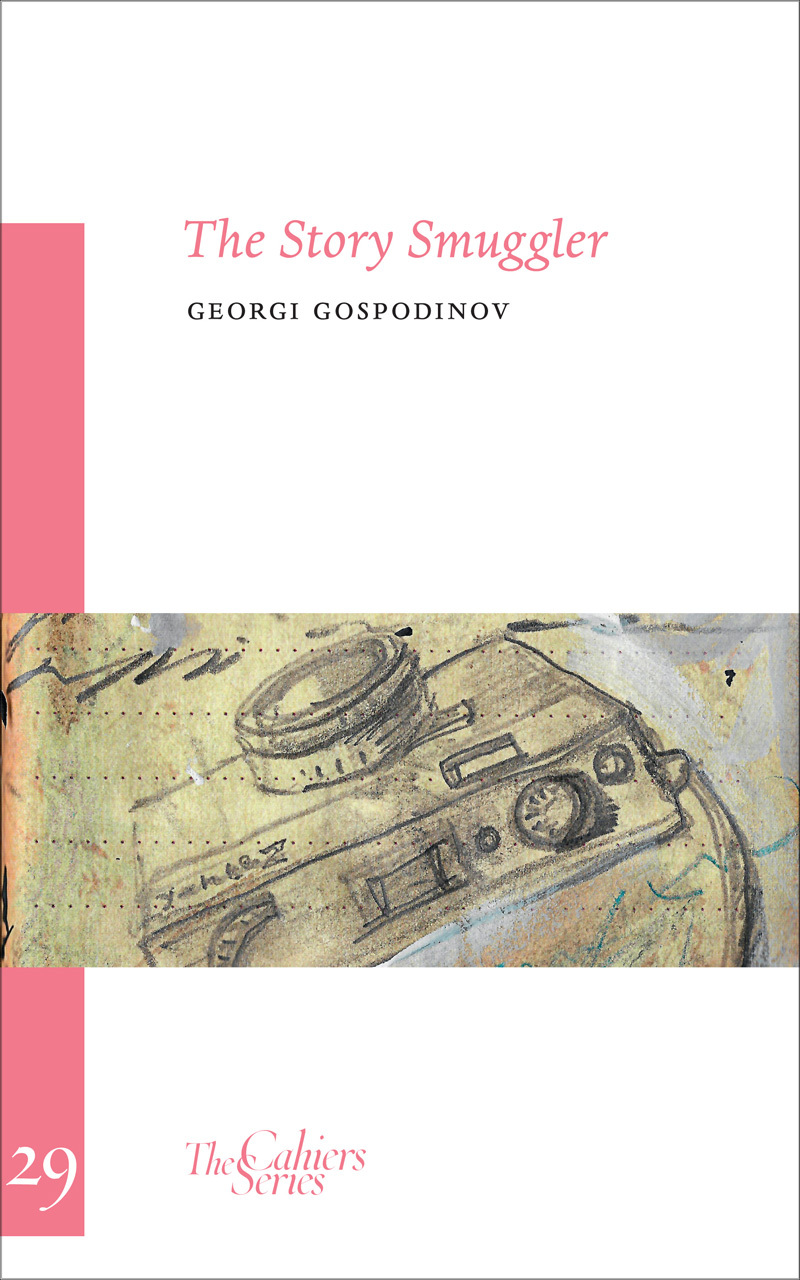
有人走私烟酒,有人走私武器,而对于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来说,最危险的违禁品是作家偷偷携带过境的故事。在《故事走私贩》中,戈斯波丁诺夫探讨了走私者、作家和翻译家是如何参与运送人们渴望的、有价值的、缺失的、被镇压或被禁止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戈斯波丁诺夫追溯了自己的童年,他成为一名作家的过程,并将其置于保加利亚的共产主义历史之中。借用笛卡尔的经典名言,他在写作和创造中也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支点:“我讲故事,故我在。”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降b小调
编辑:北北
图片:GETTY
iWeekly周末画报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