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ekly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被认为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也最有争议的女作家之一。她具有鲜明的激进主义倾向,也因自己的双性恋取向备受猜测。她的写作素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著称,代表作包括批评论文集《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以及小说作品《火山情人》《在美国》等。有人认为,桑塔格本身的思考和写作并不十分严谨,她更大的魅力是在于作为文化偶像,作为一个在公共领域思考和写作的女性典范,对美国当代文化产生的持久影响。然而,在桑塔格诞辰90周年,如何阐释这个文化偶像,却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把一样事物当作美来体验意味着:错误地体验它,而这是必要的。”在1977年的散文集《论摄影》结尾处,苏珊·桑塔格摘取了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权力意志》中的这句话,以阐述摄影如何使痛苦审美化。但也可以将它视作对桑塔格自己人生的注解。自20世纪60年代成名以来,苏珊·桑塔格这个名字几乎与整个当代美国文化的发展并行。作为“她这一代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桑塔格撰写了大量关于摄影、文化、媒体、疾病、人权与左翼意识形态的文章,如《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疾病的隐喻》,它们成为当代经典的重要构成部分,也使她遭遇了最为苛刻的批评,乃至当她在2004年12月28日逝世时,《纽约时报》的讣告列出了20对旁人对她截然相反的形容词:轰动性的/归于平淡的,原创的/抄袭的,天真的/世故的,平易近人的/疏远的,清教徒式的/骄奢淫逸的,真诚的/装腔作势的,深刻的/肤浅的……林林总总的评价,不断撕扯着桑塔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复杂性,但也验证着她作为一个在公共领域思考和写作的女性的魅力;而去世多年却仍鲜活地遗存在世,在文人学者的反复征引之中,更加验证了这种魅力的持久性。于是,新的问题随之产生:是什么成就了当代印象中的桑塔格?许多人都尝试对此做出回答。在法国女作家贝阿特丽丝·穆斯利(Béatrice Mousli)看来,桑塔格对爱情的终生追求构成了她作为女性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内核,欧洲文化传统奠定了她作品中的欧洲底色和人文深度;而美国作家本杰明·莫泽(Benjamin Moser)则提出,对桑塔格来说,事物与其象征、隐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正是这种焦虑推动着她的思考与写作。不尽相同的解释,孰是孰非?桑塔格诞辰90周年之际,人们仍然难以找到答案,也仍在继续寻找答案。

自我反对3岁读书,6岁写作,15岁高中毕业,17岁嫁给一个小有名气的学者——乍看之下,很容易对桑塔格的成长经历得出“早熟”的结论。但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苏珊·桑塔格,原名苏珊·罗森布拉特(Susan Rosenblatt),1933年出生于纽约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尽管,她对恪守犹太人传统身份的做法从来不屑一顾,如她后来在给小说家乔纳森·弗尔(Jonathan Foer)的回信中所写:“我没有犹太人的过去,也从未庆祝过逾越节……我是散居国外的犹太人的一部分。而且我喜欢做犹太人中的某类人,100%世俗的那类。”5岁那年,在中国做皮草生意的父亲去世,留下她和妹妹由酗酒的母亲独自抚养,桑塔格这才变得早熟而孤独。书籍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从《居里夫人》《少年维特的烦恼》《悲惨世界》,到《魔山》《荒原狼》《波士顿人》,年少的桑塔格不断探索阅读的边界与深度。母亲后来再嫁的陆军飞行员内森·桑塔格(Nathan Sontag)曾警告她:“如果你读那么多书,你将永远嫁不出去。”但她置若罔闻。她被托马斯·曼的技巧与辞藻所吸引,也为卡夫卡的叙事手法和本雅明的随笔风格所倾倒,那是与她的现实生活全然不同的文学世界。
15岁,桑塔格在日记中记下了她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女同性恋倾向”;第二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学时,她在一家书店遇到了美国女作家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描述女同性恋欲望与绝望的小说《夜林》(Nightwood),也遇到很快成为她初恋的哈里特·索默斯(Harriet Sohmers)。“你读过《夜林》吗?”这是索默斯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对自己的同性吸引力感到不安的桑塔格决心“强迫”自己“和男性发生关系”,她在学年结束时转学到芝加哥大学,与28岁的社会学讲师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热恋10天便闪电结婚,两年后生下儿子大卫·里夫(David Rieff)。这段婚姻持续了八年,直到她忍无可忍。“菲利普是一个情感极权主义者。”桑塔格在1957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她去往牛津,然后又去往巴黎,几十年里,虽未公开承认自己的双性恋身份,但却与一个又一个杰出而美丽的女性,以及男性,发生了一段又一段浪漫却注定失败的爱情,这其中包括舞蹈家露辛达·查尔斯(Lucinda Childs)和演员、电影制作人妮科尔·斯黛芬(Nicole Stéphane),当然也包括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以及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她的性生活有点像奥运会纪录。与她同代的美国女子,有多少拥有过像她那样多的男性和女性恋人,那样漂亮,那样杰出?”莫泽在《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中写道。

与桑塔格的情感生活一同翻天覆地的是她的写作生涯。巴黎时期,她深受左岸知识分子传统熏陶,阅读了大量欧洲哲学著作,但也结识了一个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等组成的先锋文化圈。在先锋文化的影响下,桑塔格于1964年发表《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Camp),从此声名鹊起。文章中,她赋予坎普(Camp)这个既有词语以新生命,将它定义为一种“对非自然之物的热爱:对技巧和夸张的热爱”,用以形容从卡拉瓦乔到王尔德,再到安迪·沃霍尔的那种标榜浮夸的美学品位,并得出最终声明:“它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是可怕的。”作为存在方式的坎普也成为桑塔格对自我的某种隐喻,她坦言“我受到坎普的强烈吸引”,“但几乎同样强烈地排斥它”。《关于“坎普”的札记》发表后,桑塔格登上《时代》封面,被誉为“曼哈顿最聪明的年轻知识分子之一”,自此,她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聚光灯下,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但正如她自己所言,她同时又深深厌弃这种过度曝光,怀疑它损伤了人的真实性。在随后出版的散文集《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中,她继续延展这种对自我的矛盾情绪。“严厉而明净的大眼睛,浅浅的笑容,黑色的衣服,低沉粗粗的声音,黑黑的长发间夹着标志性的白发”,苏珊·桑塔格因其动人心魄的美貌和出众的学问被誉为“美国文学界的黑女郎”(The Dark Lady of American Letters)。但她却对这种受膏持谨慎态度。在1975年的文章《女性之美:贬低还是力量》当中,她宣称将女性的美貌与其他美德对立起来,将使美貌在道德上受到怀疑:“我们不仅是以最大的能力把 ‘内在’(性格、智力)与 ‘外在’(容貌)分开,事实上,发现一个人既漂亮又聪明、有才华、善良的时候,我们非常惊讶。”遥相呼应着美国激进女性主义作家薇薇安·戈尼克(Vivian Gornick)在几十年后对她做出的评价:“她的美貌和性别使她获得了 ‘杰出的例外’这一独特的地位,一个被过分尊重的人物。很难不让人想象,如果她只是一个形象良好的男人,是否还会收获如此盛名。”
 △1971年,苏珊·桑塔格与约翰·列侬(左二)、大野洋子(左三)等人。难以阐释在莫泽看来,桑塔格的一生是一场在她的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之间难分胜负的战斗,充斥着外貌与性格、心灵与身体、智性与情欲之间最粗暴的对立:一个美丽而聪明的女人,她如何对自己的职业成功缺乏安全感;长期失眠、对午睡的强烈蔑视和对速度的上瘾所催生的非人生产力,如何成为她弥补社交孤立的尝试;与许多不同的人发生关系、坠入爱河,如何困扰了她对身体和精神边界的感知。“作为人的桑塔格把其他人赶跑了,但作为象征的桑塔格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因此,莫泽尝试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解读桑塔格,在所谓“酗酒的家庭制度”中理解桑塔格性格里被诟病的负面因素:“她的对手指责她太严肃、死板,缺乏幽默感,对最琐碎的事都具有掌控欲”,这是因为作为“酗酒者的孩子”,“他们成了自己父母的父母,不被允许拥有正常孩子的粗心大意,必须过早地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直到成年后, ‘格外乖’的面具滑落,显露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孩子”。莫泽诊断她患有“B型人格障碍”,症状包括“害怕被抛弃,感到难以慰藉的孤独感,从而引发疯狂的情感需求”——确实如此吗?
△1971年,苏珊·桑塔格与约翰·列侬(左二)、大野洋子(左三)等人。难以阐释在莫泽看来,桑塔格的一生是一场在她的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之间难分胜负的战斗,充斥着外貌与性格、心灵与身体、智性与情欲之间最粗暴的对立:一个美丽而聪明的女人,她如何对自己的职业成功缺乏安全感;长期失眠、对午睡的强烈蔑视和对速度的上瘾所催生的非人生产力,如何成为她弥补社交孤立的尝试;与许多不同的人发生关系、坠入爱河,如何困扰了她对身体和精神边界的感知。“作为人的桑塔格把其他人赶跑了,但作为象征的桑塔格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因此,莫泽尝试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解读桑塔格,在所谓“酗酒的家庭制度”中理解桑塔格性格里被诟病的负面因素:“她的对手指责她太严肃、死板,缺乏幽默感,对最琐碎的事都具有掌控欲”,这是因为作为“酗酒者的孩子”,“他们成了自己父母的父母,不被允许拥有正常孩子的粗心大意,必须过早地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直到成年后, ‘格外乖’的面具滑落,显露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孩子”。莫泽诊断她患有“B型人格障碍”,症状包括“害怕被抛弃,感到难以慰藉的孤独感,从而引发疯狂的情感需求”——确实如此吗?
 桑塔格的另一位传记作者贝阿特丽丝·穆斯利的视角更加克制谨慎。也许是同为女性的缘故,穆斯利对桑塔格私生活的窥探与心理动因的查寻点到为止。她充分同情桑塔格对于自身性向的困惑与痛苦,然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痛苦的表现形式:不会爱,也不会和孤独相处,只能努力塑造一个自己所向往的自我。“我梦故我在”,这句桑塔格写在长篇小说处女作《恩主》开头的句子,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名言的改写,在穆斯利笔下,也成为桑塔格人生状态的写照。追逐一生的恋情与恋情之殇锻造了她的女性主义底色,同文艺界人士的交往缔造了她审视世界的方式与对艺术的别样感受力,然而面对精神与肉体、梦境与现实的断裂,她“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我既没有精神,也没有希望”。文学批评家黛博拉·尼尔森(Deborah Nelson)则将桑塔格内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差距归入一种“辩证的统一”。她指出,桑塔格的写作具有一种以联想和格言的方式谈论激情,却能够避免沉溺其中的迷人风格,并认为桑塔格的这种对冷静的审美智性的拥抱,正是在她饱含欲望和痛苦的个人经历中获得了更强烈的反馈,同时也成为对她所生活着的“充满情感强度与无力感的浪漫戏剧”的批判性拒绝。一种“自律的自我超越”,既引导着读者进入感受、依恋与脆弱的世界,也标举着她自身对这种感受、依恋与脆弱的拒斥。
桑塔格的另一位传记作者贝阿特丽丝·穆斯利的视角更加克制谨慎。也许是同为女性的缘故,穆斯利对桑塔格私生活的窥探与心理动因的查寻点到为止。她充分同情桑塔格对于自身性向的困惑与痛苦,然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痛苦的表现形式:不会爱,也不会和孤独相处,只能努力塑造一个自己所向往的自我。“我梦故我在”,这句桑塔格写在长篇小说处女作《恩主》开头的句子,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名言的改写,在穆斯利笔下,也成为桑塔格人生状态的写照。追逐一生的恋情与恋情之殇锻造了她的女性主义底色,同文艺界人士的交往缔造了她审视世界的方式与对艺术的别样感受力,然而面对精神与肉体、梦境与现实的断裂,她“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我既没有精神,也没有希望”。文学批评家黛博拉·尼尔森(Deborah Nelson)则将桑塔格内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差距归入一种“辩证的统一”。她指出,桑塔格的写作具有一种以联想和格言的方式谈论激情,却能够避免沉溺其中的迷人风格,并认为桑塔格的这种对冷静的审美智性的拥抱,正是在她饱含欲望和痛苦的个人经历中获得了更强烈的反馈,同时也成为对她所生活着的“充满情感强度与无力感的浪漫戏剧”的批判性拒绝。一种“自律的自我超越”,既引导着读者进入感受、依恋与脆弱的世界,也标举着她自身对这种感受、依恋与脆弱的拒斥。 △1968年,苏珊·桑塔格执导电影《食人族二重奏》现场,与摄影师拉斯·斯万伯格(Lars Swanberg)。
△1968年,苏珊·桑塔格执导电影《食人族二重奏》现场,与摄影师拉斯·斯万伯格(Lars Swanberg)。
哪一种阐释更加接近真正的苏珊·桑塔格?也许哪一种都不是。在桑塔格之子大卫·里夫的回忆录《死海浮沉》(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中,里夫描绘了桑塔格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所表达的对死亡的强烈恐惧与对生的渴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的母亲还没有活够。她陶醉于存在本身。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像她那样毫不含糊地热爱生活。”的确,她还没有活够。即便晚年,桑塔格也在不断如获新生。在冷战高峰的那些年月里,她投身政治浪潮,成为反对越战的知识分子中流砥柱,她呼吁人们理解古巴革命,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奔赴萨拉热窝,她也批评“9·11”事件爆发是对美国强权的报复。她总在不断提出新的反对与反思,对外界,也对自我。似乎终其一生,在她那满世界飞奔的旅程、眼花缭乱的情史、多领域交叉涉足的论著之中,她不过都在重复同一件事:阐释自我,然后再抵抗这种阐释。
内容来源于《周末画报》
撰文—之白
编辑—喜乐
图片—视觉中国、东方IC、AFP
iWeekly周末画报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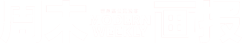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